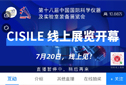近年來,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和國際政治資源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大國之間圍繞核心關鍵技術的競爭日趨激烈,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最新態勢,并體現與國際權力斗爭密切相關的政治邏輯。
一、國際科技競爭的最新態勢
一是謀劃布局新興和前沿技術,爭取主導未來產業。人工智能、3D打印、先進分析技術、先進材料、先進機器人、區塊鏈、網絡安全、數字設計、高性能計算、人機交互和物聯網等領域成為各國競逐的前沿技術。如美國計劃從2021年起5年內,新增緊急撥款520億美元用于芯片和5G領域研發。日本宣布2022年設立一項1000億日元(約合9億美元)的基金,助力半導體、蓄電池、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研發工作。德國計劃到2025年投入30億歐元用于人工智能核心關鍵技術研發。同時,各國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應用和商業化,通過設立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政產學研合作開展技術攻關、對成果轉化給予稅收優惠等措施,努力把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
二是強調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可控與供應鏈安全。隨著科技“脫鉤”和關鍵材料、器件、零部件供應中斷威脅日益嚴峻,各個國家對于掌握戰略性產業核心關鍵技術的重視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使各國對于供應鏈安全更加關注。美國商務部等部門負責評估信息與通信技術、生物醫藥與健康、能源、食品與農業等產業供應鏈安全,并向美國總統提交年度報告。美國國防部采取各種措施保障國防電子元器件供應鏈安全:積極構建本土完整的供應鏈,防范供應中斷隱患,補助527億美元吸引臺積電、三星、格芯等芯片制造商在美國設廠;加強風險管控確保供應鏈安全可靠,開展安全技術研發,溯源偽冒和惡意篡改產品;創新采購模式,保障過時元器件的供應,解決武器系統的可靠性、可維護性和老化過時技術支持等問題。
三是美國謀求主導建立“基于價值觀”的國際科技聯盟。2021年3月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民主技術合作法案》,以捍衛民主制度、規范和價值為由,號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英國等所謂的“全球民主國家”建立多邊科技政策協調框架,確保美國對世界技術的領導權。2021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首腦的“四方峰會”上提出建立科技合作框架。2021年6月8日,《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中還公布一份全面針對中國的區域戰略,其強調通過加強與歐洲等國家的伙伴關系以制衡中國。歐盟委員會則于2021年5月18日發布《全球研究與創新方法:變化世界中的歐洲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強調在國際研究與創新合作中推動“以歐盟基本價值觀為基礎的公平競爭與對等原則”。歐盟視中國為“應對全球挑戰的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認為出現了與美國“重振研究與創新合作關系的機會”。
四是加大管控力度和限制先進技術外流,限制外國投資關鍵和敏感技術領域。2018年8月,美國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涉及關鍵設施、關鍵技術和敏感數據等領域的任何股權投資的審核權力;2018年11月,歐盟通過關于審批威脅國家安全的海外直接投資法律提案,涉及芯片、通信、人工智能、醫療服務和生命科學等領域。同時,協力加強技術出口管制。美國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授權美國商務部對涉及國家安全但未被美國《出口管理條例》涵蓋的新興和基礎技術出口、再出口或國內技術轉移進行管制,使管制范圍擴大、關口前移,并積極加強與《瓦森納協定》等多邊體系協同合作,收緊多邊出口管制。
二、技術權力視域下國際科技競爭的政治邏輯與目的
隨著科技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對世界政治具有塑造作用這一觀點已在學術界形成廣泛共識。國內外學者就科技競爭與國際關系的相互作用進行了多方位探索,試圖闡明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技術和技術競爭與國際關系核心要素(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
2.1 國際科技競爭的政治邏輯
中國對國際科技競爭的研究側重于科技在國際競爭中的作用。李濱等認為,在等級化的國際生產關系中,國家的科技水平決定了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表現為邊緣國家對核心國家的依附關系;核心國家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壟斷核心技術,維護現有國際分工體系及既定國際利益分配格局。肖洋指出,科技優勢是霸權國家的力量基石,標準霸權則是霸權可持續的保障;國際標準制定權決定了產業主導權和競爭優勢,因而成為國際政治經貿博弈的焦點和貿易壁壘的新載體,國際標準制定權爭奪的目的是維護科技霸權。王悠等指出,科技已經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一種結構性權力,“科技帝國主義”對經濟開放、多邊機構、安全合作和團結民主等傳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提出挑戰;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有望從根本上改變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削弱國際秩序包容性,并使國際權力分布極端化。林濤借鑒結構性權力論,提出可以從生產、安全與知識3個角度理解科技對國際關系權力的影響機制,國家“綜合權力”的增長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科技通過影響其他權力結構來實現“綜合權力”增長。張倩雨進一步提出技術權力的概念,指出技術權力是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和技術實力,影響和支配世界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國際關系的權力。池志培則提出以技術政治代替地緣政治,指出技術政治是國家間為了實現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技術競爭,是通過技術優勢獲得政治優勢的國家間政治角力。
孫海泳認為國外對國際科技競爭的研究側重于從技術本質層面關注科技與國際關系。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政治學者丹尼爾·W.德雷茲內(Daniel W.Drezner)提出,技術是影響國際關系的一個獨立變量,但世界政治的性質也影響技術變革的步伐。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助理教授杰弗里·L.赫雷拉(Geoffrey L.Herrera)認為,技術發展受制于政治主張,本質上是政治性的議題,是國際政治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英國薩塞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教授丹尼爾·R.麥卡錫(Daniel R.McCarthy)認為,具有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的技術體系在國際環境中能夠發揮一種特定類型的決定主義作用,技術發展導致國內、國際體系的變革,關乎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美國鮑林格林州立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副教授斯蒂芬·H.弗里奇(Stefan H.Fritsch)指出,技術是全球體系結構變化和轉型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但國際政治經濟學長期將技術視為影響全球事務的間接因素,而忽視了技術也可以作為直接動因。
這些研究對于理解當前國際科技競爭的政治邏輯是非常有益的。但一部分研究受現實主義物質權力觀的影響,沒有擺脫技術工具論的束縛。另一部分研究雖然指出技術工具論的局限,但尚未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正如倫敦大學學院的網絡安全和全球政治教授瑪德琳·卡爾(Madeline Carr)所言,現有分析技術與權力關系的方法是在工業技術的背景下發展而來的,難以應對信息時代下權力本質的復雜性,因而限制了對技術與權力關系更深層次的研究。
鑒于此,本文根據馬克思技術批判思想和西方學者的技術政治理論,結合對全球社會技術系統的分析,提出國際技術權力概念,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國際科技競爭的政治意涵和內在邏輯。本文認為國際技術權力是國際關系行為者憑借其在某一領域的技術主導優勢,通過全球社會技術系統將技術規則和主體意志加諸于系統內其他行為者以獲取自身利益的能力。
社會技術系統是技術規范融入社會組織并與其中的各種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會協作系統。實證研究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行業已經展現出全球高度一致的技術規范和社會技術秩序。有關全球生產網絡和價值鏈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許多行業組織已經超越區域和國家領土的地理邊界,主導行業生產和科技創新。所以,社會技術系統已經演進為全球化系統,形成全球社會技術秩序。
國際技術權力在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通過居于主導地位的參與者將技術規范擴散到全世界不同地方而得以實現。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技術優勢使主導者處于全球生產網絡的有利地位,并轉化為謀求經濟、軍事、社會等領域利益的工具,體現了技術權力的工具屬性;另一方面,由于價值觀隨著技術規范擴散而傳播,通過全球社會技術系統的傳導得以把主導者的主體意志強加給系統中的其他行為者,體現了技術權力的社會屬性。國際技術權力的概念充分詮釋了技術以及圍繞先進前沿技術的國際競爭與國際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了國際科技競爭的政治邏輯。
2.2 國際科技競爭的目的
大國圍繞核心關鍵技術競爭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其在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的技術權力,進而強化自身國際霸權基礎,這是由技術作為重要國際政治資源的屬性決定的。
其一,技術是國際經濟競爭的關鍵。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的國家意味著在全球經濟產業結構中處于價值鏈的高端,有利于實現國家經濟利益。同時,科技創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運用極有可能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掌握顛覆性技術的國家將主導新的國際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并通過技術標準和專利等措施鎖定國家經濟利益。所以,當前國際科技競爭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強調把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并確保重要產業供應鏈安全可控。
其二,技術是地緣政治權力的重要支柱。美國為了開展大國科技競爭,牽頭成立了一系列的國際技術聯盟。無論是以“五眼聯盟”為基礎的多邊科技政策協調框架,還是以“印太戰略”為著眼點的“四國聯盟”,都帶著鮮明的地緣政治色彩,服務于地緣政治博弈。同時,大國間的核平衡和全球化的發展使其出現直接沖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布局新興前沿技術時,對人工智能、互(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尤為關注,因為它們可能改變未來戰爭與沖突的模式,在地緣政治斗爭中具有重大戰略價值。
其三,技術是重要的對外政策議題,影響國家外交能力。隨著科技地位日益重要,對外科技政策能夠作為安全政策工具在國際博弈中發揮制衡作用。無論是限制外資投資關鍵敏感技術領域,還是強化技術出口管制,都是為了鞏固自身優勢地位,壓制和削弱對手的競爭能力。美國《1979年出口管理法》在1994年到期后,由于國內政治斗爭無法達成統一的修訂共識,長期依靠美國總統利用《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宣布緊急狀態以維持《出口管理條例》的法律效力。為了滿足美國進行大國科技競爭的需要,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最終通過,說明技術在對外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其四,技術影響國家的綜合國力進而決定國際權力格局。綜合國力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發展并發揮對外影響的各種力量的總和,包括經濟、政治、科技、軍事、外交和文化等各種實力,以及國家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等基礎條件。科技除了對經濟、軍事和外交實力產生深刻影響外,還廣泛作用于政治、文化和人力資源等要素,對國家綜合國力起決定性作用,從而決定國際權力的基本格局。
三、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技術權力的實現過程
國際科技競爭的目的是為了最終奪取國際政治權力,其本身也是實現國際政治權力的過程,這是由于當今時代科學技術已經深刻嵌入全球社會技術系統,技術規則已經成為社會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將美國對華為的打壓作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自2018年以來,為了應對華為在5G領域的競爭,美國不惜動用一切國家力量全面封殺,維護其即將失去的技術優勢,實現技術霸權的意圖十分明顯。事件的起因是在5G技術標準制定中,華為主推的極化碼(polar code)方案成了5G控制信道eMBB(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場景的編碼標準。這既是華為等中國企業在技術研發、專利布局等方面多年厚積薄發的成果,也與當前通信技術復雜化和專利標準碎片化密切相關。在5G標準的專利組合中,華為公司和三星公司的核心技術分布相似,雖然總體實力弱于美國高通公司和IDAC公司,但在數字信息傳輸的載波調制系統方面具有優勢。憑借在整個技術標準中的關鍵技術布局,華為在eMBB場景的編碼標準中獲得競爭主動權,從而動搖了美國在信息與通信技術(ICT)領域的主導地位。
美國為了維護技術霸權,在信息與通信技術領域的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對華為實施了極限施壓,充分展現技術權力的一種實現過程。
一是將華為的技術意識形態化。攻擊華為技術違背西方“普世價值”,指責華為違反了美國對伊朗、朝鮮的制裁,危害美國國家安全。以此為借口,美國先后將華為在世界各地的114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限制技術和市場準入。
二是構建打壓華為的5G技術聯盟。2019年5月,美國牽頭召開布拉格5G安全大會。美國、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32個國家以及4個全球移動網絡組織聯合發布了“布拉格提案”,將5G安全聚焦供應商和供應商所在國,提醒各國政府不要依賴那些容易受國家影響或尚未簽署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協議國家的5G通信系統供應商。通過布拉格5G安全大會機制,美國聯合盟友抵制華為的5G設備和技術。
三是利用芯片制造技術優勢扼殺華為。由于在5G標準制定中華為占據了先機,加上中國完善的供應鏈配套體系,美國如果僅僅聚焦5G應用領域已經無法遏制華為。為了維護技術霸權,美國先是運用《出口管理條例》中限制交易的規定,即使用美國零配件或技術超過25%制造的產品不得銷售予華為,企圖阻斷華為的芯片供應。在無法達成目標后,又把這個比例下調至10%,從而徹底破壞華為的供應鏈,使華為即使擁有先進的芯片設計技術也無法轉化為產品。
四是將技術霸權“合法化”。2018年底,加拿大應美國要求逮捕了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并在2019年1月以23項貿易情報竊取和欺詐罪名起訴華為。關鍵案由是指控孟晚舟在2013年8月就華為與星通技術有限公司的關系向匯豐銀行做了虛假陳述。雖然在中國政府努力下,2021年9月孟晚舟獲釋回到中國,但美國通過這一案件,借用司法手段粉飾其“長臂管轄”的霸凌行徑,借以維護其技術霸權的“合法性”。
數字經濟是各國重要的戰略性產業,圍繞信息與通信技術的上下游產業鏈是當今最復雜、最重要的全球社會技術系統。由于現代信息技術以芯片制造為基礎,所以美國借助芯片制造關鍵環節和整體技術優勢,以及與其他先進西方國家的技術聯盟,意圖保持其在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的霸權地位,維護技術權力。這充分說明,圍繞關鍵核心技術的國際競爭,本質上既是對政治權力的爭奪,又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其“普世價值”,把出口管制、“長臂管轄”等域外法權強加給其他國家,實現其國際技術權力的過程。
四、技術權力視域下國際科技競爭研究路徑
國際技術權力概念有4個關鍵點值得注意:一是權力主體是擁有技術主導優勢的國際關系行為者,其既可以是國家、跨國公司、國際技術組織,也可以是它們的聯盟;二是權力客體(權力相對人)是特定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除權力主體外的其他行為者,包括各類組織和個人;三是權力通過具體的技術產業領域和與之對應的全球社會技術系統發揮作用,調節組織與組織、組織與人、人與人的關系;四是權力包含技術規則和權力主體的意志,具有特定價值取向。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國際技術權力概念為理解技術在國際權力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從不同方面對國際技術權力概念進行深入研究,為制定國際科技競爭戰略帶來有益的政策啟示,以下從3個方面分析其研究路徑及潛在意義:
一是對國際技術權力主體進行深入研究。國家并非技術權力的唯一主體,跨國公司、國際技術組織、科研聯合體,以及它們的聯盟都可以成為技術權力的主體。主體的多樣性決定了利益的差異性和目標的多元性。結合具體的產業技術領域對技術權力主體不同的利益訴求進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其在主導者的技術統治中尋找重塑社會技術系統的突破口。同時,主體多樣性意味著其結構的復雜性,可以為實施差異化的國際科技合作策略創造條件。例如,對當前西方國家各種“技術聯盟”復雜的分層供應鏈體系進行剖析,可能會對打破技術封鎖有所裨益。
二是深入分析國際技術權力發揮作用的機制。技術權力不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產生于一定的產業技術領域,通過特定的全球社會技術系統發揮作用。全球社會技術系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網絡,深入分析其關鍵節點可以為技術攻關和技術超越確定方向。同時,不同產業技術領域在國際綜合國力競爭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結合自身實際分析相關領域技術權力發生作用的機制,有助于國家確定科技競爭的重點方向。例如,結合國際形勢和技術基礎,分析自身在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的優勢和劣勢,研究確定產業政策重點方向、技術攻關主要領域、基礎研究長遠布局、人才引育目標路徑等。
三是深入分析國際技術權力的社會屬性。技術權力具有的社會屬性,以及其通過技術規則直接作用于全球社會技術系統中的組織和個人的事實表明,技術應用能夠深刻塑造包括國際關系在內的人類社會關系,由此技術倫理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深入分析技術權力的社會屬性及其對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深刻影響,使不同文化和制度的行為者在面對主導者時通過更加人道的技術倫理和更加民主的技術演變進程,處于更加有利的國際地位。當前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等新一輪科技革命與人類自身命運緊密相連,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外交方略的大國,對科技倫理和創新治理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五、結語
愈演愈烈的國際科技競爭充分顯示技術已日益成為影響和塑造國際關系的關鍵要素。國際技術權力概念的提出很好地詮釋了國際科技競爭的政治意涵和內在邏輯。本文對國際技術權力的多角度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拓展國家科技戰略的視野,啟迪科技政策的制定,并為構建國際科技競爭的理論分析框架提供一種新視角。
作者:吳漢榮,廣州市科學技術局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科情智庫,原載于《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23年3月第38卷第3期